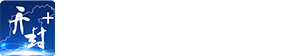为政之要莫如得人
作为政治家、史学家,司马光当然深知人才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。这位一生对北宋朝廷都忠心耿耿的四朝元老,在人才问题上多有精辟论述。
熙宁元年(1068年),神宗问起富民之术,司马光明确回答说:“凡富民之本,在得人。”次年,在与神宗的对话中他又说:“苟得其人,则无患法之不善;不得其人,虽有善法,失先后之施矣。”如果有了人才,就不用担心法令不好;不得人才,就是有好的法令也难以施行。
司马光和几个助手一起,“鉴前世之兴衰,考当今之得失”,完成皇皇巨著《资治通鉴》。在《资治通鉴》中,司马光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,用大量篇幅来讲述历史上选人、用人的故事,并以此阐发他的人才主张。在卷7中,司马光说“为国家者,任官以才”;在卷73中,他说“为治之要,莫先于用人”;在卷138中他还说“举贤才以任百官,修政事以利百姓,则封域之内无不得其所矣”。
元祐元年(1086年),已到临终之时的司马光,还给哲宗上奏说:“为政之要,莫如得人,百官称职,则万务咸治。”
才与德异德帅才资
关于人才标准,司马光同样坚持德才兼备的人才观,但在二者关系上,他尤其强调“德”的重要性。
在嘉祐六年(1061年)的《论选举状》中,司马光就说过:“取士之道,当以德行为先,其次经术,其次政事,其次艺能。”与经术、政事、艺能相比,德行是第一位的。
在《资治通鉴》卷1中,司马光根据战国时期晋国魏氏、韩氏、赵氏三大家族联合消灭智氏家族的历史,写下一篇400多字的“臣光曰”。文章开篇他就指出:“才与德异,而世俗莫之能辨,通谓之贤,此其所以失人也。”他认为才与德是两码事,搞不清楚二者区别,一概称之为贤人,那就会看错人、用错人。
既然“才与德异”,那么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?司马光接着说:“聪察强毅之谓才,正直中和之谓德。”才是指一个人的聪明才智,观察敏锐、行事果断;德是指一个人的修养品格,公正刚直、中正平和。
但是才与德的地位和作用不同,对此司马光强调说:“才者,德之资也;德者,才之帅也。”也就是说才是德的凭借、依靠,而德是才的统帅、主导。德才相比,德是第一位标准,才是第二位标准。智氏家族之所以被灭,就是因为这个家族的接班人智伯“才胜德也”,处事霸道、利令智昏、不讲仁德。
依此标准,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:“才德全尽谓之圣人,才德兼亡谓之愚人,德胜才谓之君子,才胜德谓之小人。”所以在选拔、任用人的问题上,他提出:“苟不得圣人、君子而与之,与其得小人,不若得愚人。”为什么?因为“君子挟才以为善,小人挟才以为恶。挟才以为善者,善无不至矣;挟才以为恶者,恶亦无不至矣。愚者虽欲为不善,智不能周,力不能胜,譬如乳狗搏人,人得而制之。小人智足以遂其奸,勇足以决其暴,是虎而翼者也,其为害岂不多哉!”君子凭借才能做善事,善事就会到来;小人凭借才能做坏事,坏事也会到来。愚人虽然想做坏事,但由于智力不足、能力不够,就像小狗咬人,是能够被制服的。而小人就不同了,他有足够的智谋去做坏事,有足够的力量施行残暴,就像恶虎添翼一样为害甚多。可见小人坚决不能任用。
文章最后司马光提醒说:“德者人之所严,而才者人之所爱;爱者易亲,严者易疏,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。自古昔以来,国之乱臣,家之败子,才有余而德不足,以至于颠覆者多矣,岂特智伯哉!”有德之人令人敬畏,容易疏远;有才之人叫人可爱,容易亲近,考察的人多被才能所蒙蔽而忘了品德,乱国之臣、败家之子才有余而德不足,以至于覆败、灭亡的太多了,所以“为国为家者,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,又何失人之足患哉”。
司马光纵观历史兴亡变迁,在人才问题上提出才与德异、德统帅才的思想,识人用人要搞清楚孰轻孰重、孰先孰后,这实在弥足珍贵。
唯贤是举用人所长
《尚书》曾说:“野无遗贤,万邦咸宁。”朝野上下、闹市僻壤皆有贤才,就看用人者有没有识才慧眼、用贤诚意了。
嘉祐二年(1057年),司马光写下《功名论》一文,文中他说:“观之天下,乌有无士之国哉,患在人主知之不明,用之不固,信之不专耳。如是,则人臣虽有才智而不得施,虽有忠信而不敢效,人主徒忧劳于上,欲治而愈乱,欲安而愈危,欲荣而愈辱矣。”治理好国家,君主不可能也不应该事必躬亲,必须依靠人才,对人才要做到知之明、用之固、信之专。
为防止野有遗贤,司马光还主张众人举才、凭公取才。在《资治通鉴》卷225中他说:“天下之贤,固非一人所能尽也,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,所遗亦多矣。古之为相者则不然,举之以众,取之以公。众曰贤矣,己虽不知其详,姑用之,待其无功,然后退之,有功则进之。所举得其人则赏之,非其人则罚之。进退赏罚,皆众人所共然也,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。苟推是心以行之,又何遗贤旷官之足病哉。”
据此司马光反对凭门第、资历、亲疏选人用人,主张用人不徇私情:“用人者,无亲疏、新故之殊,唯贤、不肖为察。”在《资治通鉴》卷140中,他对魏晋时期“先门第而后贤才”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,说这是“魏晋之深弊也”,并明确提出:“君子小人,不在于世禄与侧微。”
既然天下贤才众多,司马光还要求朝廷要礼贤下士,诚心招才。在《资治通鉴》卷51中他说:对于“道德足以尊主,智能足以庇民”的贤能之士,为君者要“尽礼以致之,屈体以下之,虚心以访之,克己以从之”,不要“徇世俗之耳目”。
不仅如此,司马光还提出要依靠众人秉公举贤。在《资治通鉴》卷225中他说:“其人未必贤也,以亲故而取之,固非公也;苟贤矣,以亲故而舍之,亦非公也。”为防止“请托欺罔”发生,“举得其人则赏之,非其人则罚之”。
至于如何做到知人善任,司马光给出的原则是“至公至明”。
司马光认为,用人“当容其短,收其所长”,量才使用。元祐元年(1086年)他上奏哲宗曰:“为政得人则治。人之才,或长于此而短于彼,虽皋、夔、稷、契,各守一官,中人安可求备?若指瑕掩善,则朝无可用之人;苟随器授任,则世无可弃之士。”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,用人要量才而用,“精择其人,使之各举其职”,人尽其才,才尽其用。如果求全责备,那就没有可用之人了。所以他在《资治通鉴》卷73中说,“记览博洽,讲论精通”,这就是善于治经之士;“曲尽情伪,无所冤抑”,这就是善于治狱之士;“仓库盈实,百姓富给”,这就是善于治财之士;“战胜攻取,敌人畏服”,这就是善于治兵之士。“至于百官,莫不皆然”,考核官吏就以此为据。作为人君,不能“以亲疏贵贱异其心,喜怒好恶乱其志”。
用人不疑赏善罚恶
在用人问题上,司马光主张选才必精、用人必专,对于选用的人才要放手使用,做到用人不疑。他在《功名论》中提出:“臣有事业,君不信任之,则不能以成。”如果“人主有贤不能知,与无贤同;知而不能用,与不知同;用而不能信,与不用同。不用贤而求功业之美、名誉之白,难矣”。天下有的是贤才,为君者只有做到知贤、用贤、信贤,才能求得好的功业和名誉。
在《资治通鉴》中,司马光也多次借历史经验教训阐发用人不疑的道理。在卷100中他说,如果“知其不忠,则勿任而已矣。任以大柄,又从而猜之,鲜有不召乱者也”。在卷118中,他赞同古人所说“疑则勿任,任则勿疑”。
使用人才必须赏善罚恶、赏罚分明,这也是司马光人才思想的重要方面,对此他多次上疏阐述这个道理。在《乞优赏宋昌言札子》中他说“国家大政,在于赏罚”;在《言御臣上殿札子》中,针对北宋王朝多年来用人不问政绩、只靠资历升迁的弊端,他提出:“致治之道无他,在三而已:一曰任官,二曰信赏,三曰必罚。”在嘉祐八年(1063年)上仁宗疏中他说:“为政之要,在于用人,赏善罚恶而已。”在治平二年(1065年)给英宗上疏中他还说:“选用英俊,循名责实,赏功罚罪。”
在《资治通鉴》中,司马光以史为鉴,也多次阐述赏罚的道理。在卷28中他说“人君者,察美恶,辨是非,赏以劝善,罚以惩奸,所以为治也”;在卷79中他说“政之大本,在于刑赏。刑赏不明,政何以成”;在卷172中他说“赏有功,诛有罪,此人君之任也”;在卷194中他还说“有功不赏,有罪不诛,虽尧舜不能为治,况他人乎”。
司马光的一生,无论是为官还是做人,他都严以律己,脚踏实地,廉洁奉公,光明正直。他和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是非功过虽有争议,但其丰富的人才思想却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。